2021年6月,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IESR)与全球劳动组织(The Global Labor Organization, GLO)通过线上平台共同组织了第四届IESR-GLO联合会议。近20位来自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东京大学、国立首尔大学、哥德堡大学、乔治亚大学、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南大学等海内外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专家学者受邀相聚云端,从经济学的角度,围绕各个国家不同的社会保障制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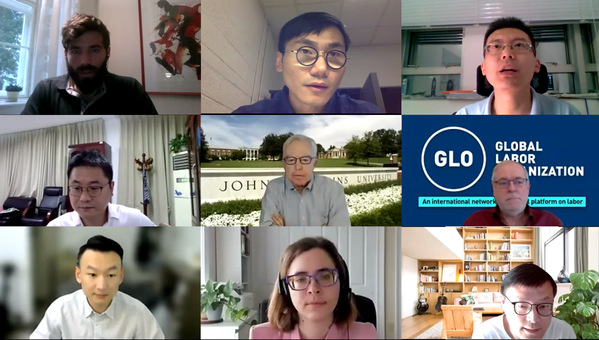
线上会议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Robert Moffitt教授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Timothy Smeeding教授受邀担任本次会议的主讲嘉宾。Robert Moffitt教授的演讲主题为 “Take-up in social assistance programs: theory and evidence”,他从理论和实证方面分析了测量、成本、社会污名、信息和制度约束等对社会救助覆盖面的影响。

Robert Moffitt教授
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17个目标中的第1个,为此世界各国政府和组织都重点关注加强社会救助和转移支付等社会保障制度,尤其是扩大覆盖面。社会救助旨在保证每位公民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然而社会救助并不总能为目标人群提供支持,如果钱越多越好,为什么有人并不乐意拾起十字街头的一元钱?为什么不同社会救助项目的覆盖面存在巨大差异?Moffitt教授从测量误差、参与成本、社会污名、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项目制度约束等角度来提供解释。
首先,社会救助覆盖面的测算存在一定的测量误差,不同的项目适用于不同的数据和衡量标准,对象界定的复杂程度也会影响其准确核定。而且高社会救助水平会激励人减少劳动供给、减少甚至瞒报收入,这种“养懒汉”和“隐性就业”现象会高估社会救助覆盖面。但这些误测相比起福利缺失仍是次要的。
其次,参与社会救助项目需要付出一定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成本,较高的参与成本会降低人们申请社会救助的激励(Currie and Grogger 2002)。但是这些成本也作为一种信号甄别机制,一定程度上能减少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更精准识别救助最需要救助的人。
再次,出于自尊和社会的偏见歧视的社会救助污名化,也会减少人们参与社会救助。Moffitt教授将参与社会救助的羞辱感视为成本引入效用最大化模型,发现其存在会导致多重均衡。Fraker and Moffitt (1988)通过研究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援助(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 AFDC)和食品券(Food Stamps),发现两个项目的羞辱感正相关,参加一个项目的人有更高概率参加另一个项目。
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导致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一直是社会救助的难点重点。DaPonte (1999)通过随机对照试验验证了提供更多信息能够减少人们参与社会救助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从而提高参与概率,并且收入更低、能从救助项目获益更多的人有更多激励来获取信息。政策制定者还可以用配额、是否附加条件等制度约束来“选择”接受社会救助的人。
社会救助的目标是让最需要社会救助,即社会救助边际效用最高的人接受社会救助,然而参与成本、羞辱感和不确定性等会导致稀缺的救助资源并不都能配置到最需要的人手中,因此实现精准有效的社会救助需要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Moffitt教授接着讨论了我国的低保制度,这项建立于九十年代的无附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制度,已纳入各级财政预算,由当地人民政府确定、执行和调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对象的资格认定是低保的突出问题,“人情保、关系保、错保、漏保”屡禁不止,并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域差异。这部分是由于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尤其在农村地区,很难准确衡量并核实作为界定低保主要依据的家庭收入。Moffitt教授认为实现低保“应保尽保、应救尽救”的主要障碍并不在于侮辱感、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参保成本,而主要是政府的制度约束。中央和各级政府需要努力奋斗,推动建立健全低保专项治理长效机制,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Timothy Smeeding教授的演讲主题为 “Poverty and Income Support Around the World: China, India and Asi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六个部分。首先,教授引入了讲座中将涉及的基本概念、统计指标和测度方法。他指出,家庭收入计划(Income Package)主要包含市场收入(MI),即通过个人努力从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储蓄或职业养老金等获得的收入;来自其他非同居家庭成员间的转移;以及公共部门的再分配。市场收入(MI)以及考虑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DI)是接下来讨论的重点。

Timothy Smeeding教授
第二部分对当今世界贫困现状进行了总结。得益于经济增长,世界减贫工作已经取得一定进展。例如第一个千年发展目标,即2015年贫困率下降至1990年的一半,于2010年提前实现。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17年发展中国家中10%以下人口的日收入低于1.90美元,远低于1990年(37%)和1981年(44%)。教授指出,随着极端贫困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接下来的研究应提高贫困线标准,如世界银行已经在$2每日的基础上增加了$3.2每日和$5.5每日的贫困线标准。
第三部分对国家间的增长和不平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分析。目前中国及部分中低收入的西方国家面临“增长红利”持续减少的问题,为此各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政策。以中国、美国和法国为例,中国的经济增长最快,但同时也面临着最严重的不平等问题:高收入群体吸纳了社会绝大部分的收入和财富,且这一比例呈持续增长态势,社会贫富分化加剧。但教授也强调,在关注相对贫困时也不能忽略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影响。当低收入群体的实际收入以每年4-5%的幅度增长时,人们通常对不平等问题采取更加宽容的态度。
第四部分利用LIS(The Luxembourg Income Study)微观数据库,对当前世界贫困现状和社会救助项目的效果进行了分析。数据显示,当前总体贫困程度最高的国家为巴西、中国、印度、南非以及老挝;很多国家存在严重的儿童贫困问题;而老年贫困问题看似严峻,但可能存在一定误导。其次从社会救助政项目的政策效果来看,亚洲国家的再分配程度较低,且对教育、健康等方面的长期人力资本投资不足;一些社会救助项目,如中国的“低保”,存在瞄准效率较低的问题。虽然相对贫困问题在发展中国家和一些金砖国家仍十分严峻,但我们也应看到经济增长带来的绝对贫困的下降。
第五部分对未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探讨。教授指出,未来研究不应局限于收入、经济增长以及减贫政策带来的短期效应,而应更多关注社会幸福感和代际流动,即代际间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变化。此外,环境恶化问题使贫困人口面临更严峻的威胁,因此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最后一部分,教授针对目前世界贫困与不平等问题提出几点政策建议。他指出应加大对人力资本,尤其是儿童人力资本的投入;增加对资本收入的征税;推行强制性的养老金固定缴款计划;促进共同繁荣和包容性增长;同时,给予劳动者更多发声的机会。
除了主题演讲,本次会议还包含政策讨论及学术报告环节,为期三天的学术盛宴因高质量的论文分享及深入充分的讨论广受好评。自IESR加入GLO成为其支持机构以来,双方不断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人口及人力资源等研究问题上,双方已顺利组织开展了四届联合会议,为该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对该领域感兴趣的普罗大众提供了一个国际化交流平台。未来,IESR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GLO提供更多支持并组织GLO在中国举办的学术活动,广邀国内外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商全球经济发展对策。
